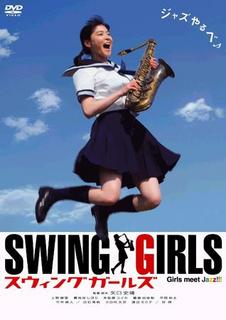訪問杜汶澤:男人很驚!沒有董建華的日子怎麼過?
這幾天,辦公室裏的人都在談「欣宜公主事件」,幾位女性同事相當氣憤,反問為什麼欣宜不能做白雪公主﹔所以當我知道有機會電話訪問杜汶澤,我劈頭第一句便問﹕為什麼男人見到欣宜扮白雪公主會好驚﹖
男人的幻想與慾望
電 話的另一端,傳來杜汶澤半醉半醒的聲線,聽起來有點性感,而且,難得他的男性身分夠赤裸,他說﹕「白雪公主、靜宜、Barbie都是有象徵意義的,白雪公 主對我這個男人來說,是遙不可及的追求對象,就像靜宜,她是東方女性的含蓄形象,Barbie則是性感代表,他們都不應由真人來扮,應該永遠是卡通人物, 要真人來扮她們,我都覺得很難頂。」
不知道杜汶澤在打圓場,還是真情剖白,卻道破了原來男人的幻想及慾望是如此脆弱,經不起真人的考驗, 只能存活於虛構的動畫人物身上,他甚至說,看到由真人來扮演米奇老鼠,即使帶頭套穿上特別服飾,也會感到有點不安,米奇老鼠也應該只是動畫﹔忽發奇想, 反迪士尼的團體,也許可以邀請杜汶澤當代言人。
杜汶澤一定是懷疑我跟一般娛記一樣,想「裝」他彈弓,所以處處防備,不想再得罪人,他反複強調,雖然自己笑過欣宜,但他並不喜歡憎恨別人,任何人身上他都能找到可愛的地方,他也很反對某周刊把欣宜造成飛鏢靶,她其實沒有做過什麼壞事……
我發現,這樣下去不是辦法,我只會重複娛樂版的調子,我怕星期日副刊的編輯不肯收貨,於是,我換個角度,把杜汶澤看成一位文化評論人,要他當專家,分析這個「欣宜」現象,杜先生似乎欣然接受。
尋找愛/恨對象:欣宜與董建華
「在我們的成長經歷中,任何人都想找尋仇恨的對象,正如人們也在不斷尋找崇拜對象,其實,我與欣宜都是他們的對象,他們不是真心憎恨欣宜,至於有人說我是『人民英雄』,其實,也不是真心崇拜。」
杜汶澤補充說,憎恨一個人的時候,經常會發現對方有值得喜愛或崇拜的地方,而當人去崇拜一個偶像時,有時也會發現一些很討厭的東西……愈說愈玄,我開始不知道他在說什麼,我乾脆問他,你崇拜誰﹖又憎恨誰呢﹖他說,這是秘密,不能告訴你。
每次談到他自己的情感時,他似乎都在迴避,娛樂圈(學術界何嘗不是﹖)也許就是這樣,大家平日都要裝得很和氣,不要得罪別人,要很有修養,不要太感情用事,偏偏娛樂版就是愛暴露這些東西﹔然而,要杜汶澤當個評論員,他很樂意,甚至跟我分析社會大勢,挺煞有介事的。
「欣 宜事件讓我們看到近年香港社會風氣有些變化,可能我們以前沒有這麼團結,現在不一樣了,自從董建華做了特首,一度成為香港人的仇恨目標,我們將所有情感都 投注在他身上,從這個角度看,董建華很『成功』,他管治我們七、八年,我們習慣了仇恨他,他 卻突然下台了,我們變得沒有目標,欣宜的出現,大家好像找到新的目標﹔香港人工作十幾小時,睡不到八小時,然後用一個小時來憎恨一個人,可能有人覺得這樣 生活會好過一點。」
這不是七一遊行後某些人說的民粹主義嗎﹖按杜汶澤的說法,欣宜比起董建華,其實是差得很遠了,欣宜只有幾百個投訴,但董建華激起五十萬人上街﹗我也有點同意他,面對曾特首的煲呔,我的確有點失落感覺,雖不至於要找欣宜作代替品。
TVB?佢唔會聽你的意見!
我們由香港社會政治大勢,談到香港文化工業。
「這 是一個人吃人的世界,我做了這一行一段時間了,我很清楚,我想,她的成長過程中,在這個階段要面對一些負面東西,是一件好事,時間尚早,你看一下謝霆鋒 (相關新聞 - 網站),他十多歲的時候便面對很多困難,現在多困難他都識笑面迎人﹔年輕遇到這些事,總好過做到幾十歲人才碰上啊﹗」
人們討論欣宜、肥肥及杜汶澤多,好像沒有人談到安排欣宜當公主的電視台,先有親吻吳卓羲,後有迪士尼開幕,有人甚至覺得電視台參與其中,製造事端,我問﹕你對TVB有什麼建議或忠告﹖
「TVB﹖ 這麼龐大的機構,通常不會接納建議,說了也是白說,哈哈,不過,作為一個製作人,要撫心自問,你真的認為她可以(扮公主),還是你早已知會有另外(反)效 果﹖如果是前者,當然沒有問題,各人有各人的美學判斷,但如果是後者,就很有問題……當然,作為藝人要懂得保護自己,藝人要磨練技藝,但同時也要懂得保護 自己,簡單來說,不要人家叫你做什麼,你便去做。」
至於反對欣宜的網民,直指「肥姐」幫欣宜上位,他們痛恨娛樂圈多「世襲」關係,多特權,杜汶澤卻有另一番見解。
不要再找真人白雪公主,追尋心中的白雪公主!
「大 家錯誤地將兩母女當成不公平代表,公平包括努力工作得到回報呀,但許多人在這個世界找不到公平,便找欣宜與肥姐出氣,其實對她們很不公平呀﹗我本人覺得情 並不是這樣,不是她們的責任,不公平的事要深究,不要只看表面,大家比較懶,覺得肥姐與欣宜就手,便拿她們當箭靶。」
杜汶澤勸香港市民盡快忘記這件事,世界有許多美好的事,盡快找一個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吧﹗繼續尋找(筆者按﹕男人的)夢想,他說,這是娛樂圈的行規,當你反對一樣東西時,請你盡快找一個另類方案﹔至於他對白雪公主的另類方案是什麼﹖
他說﹕「不要再找真人去扮白雪公主﹗」
原載:《明報》2005.9.25「星期日副刊」
照片:Mickal